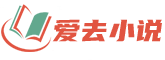“他们总是想着蜗居此处,也不想想内外局势!”
敦煌县衙内堂中,张议潭坐在左首位,语气中严厉既无奈。
张淮溶坐在他对面,张议潮坐在主位。
面对自家大兄的无奈,张议潮沉默中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随后才缓缓道:
“这也能看出来,他们已经团结起来,把想要的东西拿到了。”
他的话让张议潭等人心中一凛,张淮溶担忧道:
“这就是叔父您要进军伊州的另外原因吗,可冬季出兵伊州,这……”
“能拿下的,不必担心。”
张议潮轻飘飘一句话,便安定了张淮溶那摇动的内心。
“那刘继隆与你共事多月,你观察他如何?”
他目光看向张淮溶,张淮溶便将刘继隆这几个月的所作所为都告诉了他。
听见刘继隆将山丹治理的井井有条,即便在外作战也没有耽误山丹发展,张议潮不免露出欣慰之色。
“尚延心入寇前,他还说要训练精骑,以战养战,削弱凉州。”
“眼下有了尚婢婢相助,估计开春后他便要对凉州西边的番和动手了。”
张淮溶将刘继隆的想法说出,张议潭高兴颔首:“这倒是好办法。”
“嗯!”张议潮也认可的颔首,随后看着张淮溶继续道:
“虽说他与你和淮深相交莫逆,但他毕竟孤身一人。”
“你与他共事这几个月,可曾看出他有其它想法?”
张议潮还是忘不了刘继隆的眼神,他眼底的那丝心思让张议潮捉摸不透,只能询问张淮溶来解惑。
河西东进是大事,在这件事面前,容不得半点差错。
“倒也没有什么想法,他这人倒是好相处……”
张淮溶仔细想了想,最后摇头解释起来。
张议潭闻言也看向张议潮:“淮深拔擢他不是没有道理的,若是军中多几个刘继隆,我们也就轻松些了。”
“谈何容易……”张议潮忍不住苦笑起来。
在河西之地能还能说官话,便已经超过了九成九的人,更别提刘继隆还能写字、打仗了。
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放下后,张议潮重新看向张议潭:
“收复伊州后,便需要大兄您率精骑亲自走一趟丰州了。”
“嗯!”张议潭目光坚定:“我们派出十几批人都没有回来,这次我亲自领兵,不信到不了长安!”
“不过……”
说着说着,张议潭有些不忍的看向张议潮:
“我们说到底还是遗民,况且昔年吴氏投降吐蕃时,我张氏也并未阻拦。”
“虽说这些年我们没有助纣为虐,但朝廷那边恐怕了解之后也很难信任我们。”
面对张议潭的担忧,张议潮却语气坚定:“精诚所加,金石为开,我相信朝廷总有相信我们的一天。”
“这次大兄你前往长安,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一件事。”
张议潮缓了缓气,紧接着才担忧道:“我在河西收复失地,虽说有益于朝廷,可朝廷一开始不一定会信任我。”
“因此,我担心朝廷会……”
他顿了顿,不知道该怎么说,张议潭却抢答道:“你担心朝廷要留人作质?”
话音落下,不等张议潮开口,他便声音爽朗道:“你莫不是以为我想不到?”
“我既然选择前往长安,便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
“朝廷要人为质,淮鼎他们分量不够,河西又离不开你和淮深,那便只有我留在长安为质了。”
“呵呵……”说着说着,张议潭还笑了起来:
“去长安不用厮杀,也没有那么多事情叨扰,明明是去享福的,你不用担心我。”
他把前往长安为质说得满是好处,可张议潮与张淮溶又怎么不知道为质的下场呢。
张议潭若是前往长安为质,那除了皇帝准许,他恐怕在余生都不得离开长安城范围一步。
即便死后,恐怕也难以运回故土安葬,只能埋骨他乡。
对于乡土情结极重的汉人而言,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样结局的,更何况张议潭还要在庙堂上为河西据理力争。
哪怕他说得再如何轻松,张议潮心里始终沉甸甸的。
“好了,过几日你还要出征伊州,我便不打扰你了,你嫂嫂还等着我回去吃饭,便不留下了。”
张议潭洒脱起身,解释过后便作揖离去了。
张淮溶见状连忙跟上,走到门口才对张议潮作揖,而后离去。
瞧着他们的背影,张议潮只觉得十分疲惫,但一想到张淮深和刘继隆这些为了东归而战的年轻人,他便又觉得自己这点疲惫不算什么。
“不过半百罢了,今生还未见到长安城,何敢言累啊……”
他起身向内院走去,笑声爽朗,背影也渐渐洒脱起来。
半个月后,他如当日正厅所说般率军西征,即便敦煌已经飘雪,却无法阻止他收复伊州的决心。
刘继隆得知他出兵伊州时,却已经是十一月中旬了。
“一个月才将消息传回,这速度确实有些慢了,估计节度使都已经收复伊州了。”
山丹城外,刘继隆轻声笑着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
准确来说,他手上的并不是泥土,而是堆肥粪便与草木灰搅拌后的农家肥。
“果毅,这东西真的和牛马粪便的效果一样吗?”
崔恕皱着眉询问,面前则是占地数亩的农肥堆积地。
这些农肥堆高近七尺,不远处还有人将生粪运来,倒在地上铺开,气味难闻。
“自然可以用,明年你们就知道了。”
刘继隆笑着回应,同时不忘交代道:“这堆肥的地方你们要选好,要选在地势低洼的地方,避免生粪水渗透土中,污染地势低洼的耕地。”
“另外这些生粪变干后要和树根、树桩一起烧毁,在焚烧的过程中能把一些害虫杀死,千万不能偷懒而不处理。”
“这生粪不处理好,到时候春耕播撒便很容易祸害庄稼。”
“呕——”
刘继隆话音落下,风向突然改变,不远处的粪车吹来阵阵恶臭,崔恕这等豪强子弟哪里闻过这味道,当下便弓着身子将早饭都吐了个干净。
刘继隆倒是没吐,毕竟他前十六年当牧奴时干的恶心差事太多了。
他只是有些惋惜的看着那滩呕吐物,啧啧道:“就这么吐出来太可惜了,把它混进农肥里吧。”
“啊?”崔恕还来不及漱口擦嘴便听到这话,不免有些无语。
只可惜面前站着的人是刘继隆,他也不敢说什么。
前些日子族中传来消息,让他好好跟着刘继隆在山丹做事,显然是看中了刘继隆的潜力。
这并不奇怪,就连崔恕都早早猜到了刘继隆不会止步于小小果毅都尉之职。
光是刘继隆这些日子针对山丹军的训练,他就能猜到刘继隆接下来的目标是哪里。
“对了,李仪中何时抵达山丹?”
刘继隆转身向土道走去,崔恕连忙跟上并回应:“已经到了张掖,听说要休整半个月,估计要等月末才能到。”
“城内的院子已经为他打扫出来了,军营也已经扩建,足够容纳八百人常驻训练。”
闻言,刘继隆十分高兴,并不担心李仪中能从自己手中抢走山丹的控制权。
“嗯,等他来了,祁连城和龙首山的兵卒就能调回了。”
“眼下距离开春还有四个半月,得好好整训兵马才行。”
“仓库之中的粮食你要盯好,千万不能出了岔子,尤其要防范好水汽。”
刘继隆絮絮叨叨的交代着,崔恕则是不厌其烦的将他所说内容记下,同时汇报起军营的事情。
“果毅,军营的扫盲队人数太少了,不如请张掖调些直白过来?”
一个月前,刘继隆便将城内二十余名直白编为扫盲队,让他们对城内常驻的五百兵卒开始扫盲。
直白们都出身豪强,自然知道如何学习官话,其中音韵也都十分了解。
尽管不知道此时的大唐是否还在使用当年的河洛音,但只要把河洛音说好,基本的交流就不成问题。
“我向刺史写过信,但刺史说张掖的直白都不够用,让我暂时等着。”
刘继隆十分无奈,这个年头科举制还没有彻底完善,而且河西的豪强子弟相比较需要管理的人口来说太少,便是张淮深也找不出那么多直白给刘继隆。
张淮深让他暂时等着,其实也就是没有,想要直白只能自己找。
不过就刘继隆的背景,他是找不到什么懂文识字的人了,只能自己训练自己用。
山丹的直白都被他花钱拉拢了,况且他们也是不受本家看重的子弟,跟着他刘继隆更有前途些,所以并不抗拒教书育人的工作。
只是相比较军营里的那五百兵卒,他们更愿意教育懵懂的孩童。
然而刘继隆没有太多时间给他们教育孩童,他需要的是一两年就能用的人。
孩童虽然学得快,但毕竟经历太少,心智不成熟,很容易让人利用。
短期内,刘继隆是不打算教育太多孩童,他要等到兵卒的家属和烈属迁徙山丹后,把这些孩童集合起来,自己亲自教导。
只有这样,他才不会担心这批孩童在教育上受他人影响。
况且山丹的资源不多,培养一个孩童从目不识丁到懂文识字所消耗的资源太多,刘继隆可消耗不起。
军队扫盲只需要让兵卒知道军令含义就行,但孩童却要在日后成为刘继隆治理地方的根本,二者所需资源不可同日而语。
这般想着,刘继隆便与崔恕返回了山丹城内。
秋收过后,城内两千余百姓都被刘继隆安排了工作。
男人在城外疏通土壑、水渠,检查水车情况,并趁着枯水季高筑堤坝,收集牛羊粪便与野草、树根焚毁堆肥。
女人们则是在城内处理今年所收获的麻杆,制作冬衣。
制作麻布的流程十分麻烦,将麻杆收割后,还需要晒干、浸泡、剥皮、晒麻皮等步骤,然后麻皮撕成线,经过手搓、浸水、煮麻线等工序,才能进行织布。
棉花虽然在一百年前就传入东方,但由于此时的棉花籽多而棉绒少,故此只在西域和海南等地方有部分种植。
由于西域比较动乱,所以并没有人对传入的棉花进行选育,更没有合适棉花的棉纺技术。
正因如此,眼下百姓的冬衣,主要还是麻布填充芦絮来御寒。
只有少量的富贵人家,才能穿的上绢布、绸缎与羊绒、羽绒缝制的棉衣。
当然,河西并不缺羔羊,因此百姓的冬衣是可以填充羊绒的,只是处理羊绒比较费时间罢了。
“城内的冬衣缝制如何了?”
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刘继隆对身旁的崔恕发出询问,崔恕也解释起来。
“山丹没有被战事耽搁太久,如今已经缝制八千余件冬衣,估计月末前就能给城内所有百姓缝制三套冬衣。”
“不过张掖那边有政令,我们这边这个月得运四千件冬衣过去。”
“另外,张刺史也令我们给城外的尚婢婢他们送去一千五百余件冬衣,这一前一后便是五千五百多件。”
“这五千五百件里,还有三百件是细麻衣,消耗麻布较多。”
闻言,刘继隆询问道:“这城外麻地有多少,每年产出多少,如今库存多少,还能织多少件衣裳?”
面对询问,崔恕不急不慢的在马背上作揖交代:
“城外麻地有三千二百余亩,每亩麻地每年能收两批麻,每批产出二十余斤麻。”
“今年秋收,府库仅收上来第二批的六万七千余斤麻,若是制作粗麻衣,可制二万件左右。”
“不过按照政令,其中还要制作大约一千四百件细麻衣给张掖和山丹正九品以上的官员,所以粗麻衣顶多能制一万五千件。”
“细麻衣用鹅绒和上好的羊绒,粗麻衣用中下等的羊绒便可。”
崔恕将情况说了个清楚,刘继隆听后颔首道:
“城里用不了那么多冬衣,没人发二件冬衣便可,剩下的倒是可以在正旦(春节)的时候,给每家每户按照人头送一匹麻布,让他们自己制作夏衣。”
“这件事,你替我写文章送往张掖,相信刺史也会同意的。”
刘继隆说罢,崔恕也自然作揖应下。
二人在闲聊中不知不觉来到了衙门门口,熟练翻身下马后往城内走去。
来到正堂的时候,崔恕似乎想起什么,突然对刘继隆作揖道:
“对了果毅,听闻张长史准备在节度使收复伊州后率精骑前往丰州,准备向长安送上十州图籍。”
“张长史?”刘继隆愣了,随后才反应过来崔恕说的是张淮深的父亲张议潭。
面对这条消息,他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按照历史,张议潭此去便再也回不来了,被他寄予希望的张淮深也将在几十年后落得身首异处,满门不存的凄惨下场。
每每想起这里,刘继隆脑中便不免浮现张淮深那意气风发的身影。
二人相交莫逆,刘继隆自然不会让张淮深落得历史上那般凄惨下场,可张议潭……
刘继隆在心底叹了声气,此时的他虽然已经在河西之中有了份量,但比起沙州的那群豪强,终归是人微言轻。
张议潭这件事他阻止不了也不能阻止,因为张议潭不在长安为质,唐宣宗便不会相信他们。
于情于理,为质长安的人选都应该是张议潭。
“果毅…果毅?”
崔恕见刘继隆久久不说话,不免小声提醒起来。
刘继隆被他的呼唤声叫醒,脸上挂上一抹苦涩:“看来我们又要和回鹘这帮猪犬议和了。”
“嗯,毕竟形势如此,只能拉拢他们。”崔恕也点了点头。
“好了,说说城外的水利吧……”
刘继隆深吸一口气,将话题改换到了别的问题上。
与此同时,距山丹近千里外的一处草原上,正在爆发着血与火的争斗。
“杀!”
“胡贼娘!”
“胡杂……”
嘈杂的骂声与兵器碰撞的铮铮之声吵醒了昏暗空间内的一名汉子,他身材消瘦,目光浑浊,上身无衣衫遮蔽,满是伤口。
在他身旁,还有另外七八名受伤严重的汉子,只可惜他们受伤太重,根本说不出话来。
“遇袭了吗……”
披散头发的那汉子勉强撑起身体,浑浊的目光看着眼前的帐帘。
明明近在咫尺,可他们却被关在木牢之中,触之不及。
渐渐地,那厮杀声越来越大,越来越靠近。
“高押牙……”
躺在地上的一人虚弱着开口,勉强挤出笑容。
随着那披散头发的汉子看向他,他望着帐顶恍惚道:“若是又被掠走,你便动手给我个痛快吧……”
“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
“不行!”被称呼高押牙的男人跪下抓住此人的手:“全贞,我们不能死,哪怕就是苟且的活着也不能死。”
“沙州还在等着我们,长安还在等着我们,刺史还在等着我们!”
他一连说了许多地方,四周躺着宛若尸体的几人在听到这些地方时,都提起了一口气,勉强抽动了一下身体,证明着自己还没死去。
“去不了了,我感觉我快死了……”全贞气短,严重的伤势已经让他精神恍惚。
帐外的厮杀声越来越大,全贞的手也渐渐无力,最终从高押牙手中垂下。
“全贞!!”高押牙泣不成声,抱紧了自家兄弟的身体。
“高押牙!!”
几乎在同一时间,木牢的帐帘被掀开,一个身着明亮扎甲的汉子叫嚷着冲入帐内。
不等众人反应,他一锤砸断了木牢的木锁,单膝下跪作揖。
“丰州天德军队头李赟救人来迟,让高押牙你们受苦了!!”
汉子声音惭愧,可他却叫醒了众人。
“丰州……”
“天德军……”
几人眼神渐渐明亮起来,哪怕伤势再重,他们都挣扎着站了起来,即便摇摇欲坠。
高押牙看着眼前的李赟,眼底的泪水不知是悲伤全贞的牺牲,还是因为得救而喜极而泣。
“全贞,大唐……大唐来救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