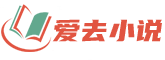“淅淅沥沥”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晨曦微露,细雨如丝,当淅沥的雨声在山丹城内外作响,不管是悲伤还是喜悦,都被这场细雨冲刷得干干净净。
衙门不远处的一座院内,雨声伴随着清脆的读书声,在清晨的空气中交织一处,声声悦耳。
朦胧的光从窗棂间透出,映照着学子们青涩的脸庞。
他们身穿粗布麻衣,皮肤黝黑却眼神明亮,朗朗的读书声中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
书声之中,偶尔夹杂着几声屋檐下的燕鸣,仿佛是天地间的和弦,为这宁静而又充满活力的早晨增添了几分生机。
随着天色渐明,城内的生活也开始苏醒。
有人烧火做饭,引得炊烟袅袅升起,屋舍内外飘散着柴火和早饭的香味。
有人穿着蓑衣,走出家门担水洗衣,清扫自家门前街道。
也有人前往了匠作坊、纺织坊等处院子,兢兢业业的工作着。
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一位过客都能感受到山丹那独特的生命力。
那些牺牲了家人的家庭已经走出阴霾,重新振作起来,试图将日子过好。
正因如此,即便是这般日子,城内最热闹的也无非两处。
一处是学堂,一处是军营。
军营门口挤满了应征入伍的男丁,学堂门口挤满了阵没将士的烈属。
男丁参军,孩童入学,这便是山丹百姓眼中的头等大事。
屋檐下,刘继隆与张淮深在学堂门口看着那一户户烈属与直白们完成入学仪式。
凉州之役,重伤残疾、阵没的将士有二百四十一人,而他们被分成两个部分。
重伤残疾、阵没将士中没有兄弟、孩子,以及有兄弟、孩子,但其年纪在十四岁以上者,可前往军营继续读书。
十四岁以下者,可直接来学堂就读。
望着上百名学子被直白们接入学堂,张淮深胸口起伏,不知该如何评价刘继隆。
“你是怎么弄来那么多书册的……”
他尽量平静着询问,刘继隆颔首道:“我改良了印刷术,让书籍可以批量生产。”
“有了书,纸张和笔墨就成了小问题,但我不知道他们日后还能不能继续读下去。”
“为什么不能?”张淮深打断,而刘继隆却看向他,沉默片刻后才道:
“我不确定日后我被调离后,接任的官员是否还愿意筹措书本纸张供他们继续读下去。”
“正因如此,我今日带刺史前来,主要就是想说说他们的问题。”
刘继隆深吸一口气,随后继续道:“收复凉州后,我希望让崔恕担任山丹的县令,因为他不会更改我的政令。”
“只要政令不改,萧规曹随的继续下去,不出十年,山丹将会为河西提供数百名身家清白的贫民读书人。”
“有了他们,节度使和你行事都能方便些,不用再束手束脚。”
刘继隆这番话说得张淮深脸色动容,不仅仅是因为他这番话有道理,更多的是为刘继隆如此无私的话所感动。
几百名读书人,这不管是放在两宋还是明清,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有了他们,张氏在河西的治理权将大大提高。
张淮深有些不敢相信,刘继隆竟然会这么大方,将他们都交给了自己。
“你把他们交给了我,那你呢……”
张淮深沉吟后开口,刘继隆却轻笑道:“我再培养一批就行。”
闻言,张淮深轻轻点头,没有拒绝刘继隆的好意。
对此,刘继隆也收回停留在他身上的目光,将目光放到了那些入学的学子身上。
数百名读书人,还是阵没将士的烈属,如此干净的家境,刘继隆又如何不心动呢?
只是他很清楚,自己拿下凉州并进驻陇南,这一过程最少需要两三年乃至三五年,并且无时无刻都在调转任职所在地。
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如何能照顾好这些需要安定下来读书的学子?
不如将他们交给张淮深,让张氏在河西的话语权稳定下来,不必再那么依赖豪强氏族。
更何况将这批学子交给张淮深他们,也有助于提升自己在河西的话语权。
至于自己,等到了陇南之后,凭借着活字印刷术,他完全可以再培养数百上千名读书人。
左右不过十年时间,以他的年纪来看,到时候也不过而立之年,足以凭借这上千读书人应对即将到来的大势。
治理一个人口万余人的小县,左右也不过需要二十几名读书人及百来名兵卒罢了。
上千名读书人,不仅可以帮刘继隆牢牢掌控陇南七州十五县,还能帮助他扩大教书班子,培养更多的读书人。
拿下陇南只是一个开始,顺应大势才是他要走的路。
这般想着,刘继隆也收敛了心神,与张淮深撑着伞往衙门走去。
倒是在他们在前往衙门的时候,此时距山丹三十余里外的龙首山谷道内,一行人马正在小心翼翼的沿着谷道往南边行走。
细雨让龙首山内的谷道不再安全,每走一段路都能发现落石和垮塌的山体。
不过十里路,这行人走了整整一个时辰才穿越大半。
不等他们继续行走,谷道上空突然响起了刺耳的哨声。
“哔哔——”
“吁!!”
听闻哨声,这一行十余人勒马驻足,四下观望起来。
不多时,马蹄声从南边的谷道传来。
不到半盏茶,十余名身着甲胄的精骑便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你们是哪家的人,来龙首山作甚!”
一名伙长策马横在两方之间,质问着这十余名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人马。
闻言,队伍中一人策马出来,恭敬行了一礼:“僧人悟真,奉节度使令前往长安归来!”
“僧人?”
“悟真?”
一时间,山丹军的兵卒面面相觑,而伙长闻言也在短暂犹豫后摆手道:“你们先跟上来!”
“多谢!”悟真舒缓了一口气,开始在山丹精骑的监督下,沿着谷道继续行走。
不过半个时辰,他们便来到了谷道口的石堡处。
石堡的校尉闻言,当即派出轻骑去山丹传信,确认悟真等人身份。
当轻骑抵达山丹时,却已经是黄昏时分,天色阴沉的可怕。
脚步声在内堂的长廊响起,不多时轻骑就被带到了内堂门口。
内堂中,刘继隆与索勋、张淮深正在品茶,见斛斯光带着轻骑到来,纷纷投来询问的目光。
斛斯光见状,将轻骑带来的悟真信物交给了刘继隆。
“折冲,这是龙首山的弟兄,他们说在龙首山的谷道发现了一群自称敦煌使者的人,领头的人叫做悟真。”
“悟真?”
不等刘继隆开口,张淮深便眼前一亮:“他们可是说从敦煌往长安而去,由长安折返回来?”
“是这么说的。”轻骑回答,而张淮深也对刘继隆解释道:
“这悟真是吴氏昔日家主,如今洪辩大德的弟子,是去年叔父他们派往长安报捷的。”
“此前高进达也提起过他们,如今看来,是他们从长安凯旋而归了!”
刘继隆自然知道悟真是谁,毕竟归义军派往长安的前面三批使臣姓名都存在于史料中,他自然不会忘记。
不过借此机会,他也倒是可以询问一下吴氏的问题。
“洪辩大德的弟子吗?那理应将他们接来山丹摆宴!”
刘继隆颔首看向斛斯光和轻骑:“你招呼这弟兄休息,另外派人前往龙首山,让王崇德派人护送悟真大德他们来山丹。”
“是!”斛斯光与轻骑作揖应下,而后退出内堂。
见他们离去,刘继隆也看向张淮深询问道:“说来,吴氏好歹也是沙州豪强,更是沙州沦陷前的刺史,为何如今不见有吴氏子弟担任要职?”
“这个嘛……”张淮深深吸一口气,随后娓娓道来。
吴氏的来历,主要源于百年前的沙州刺史吴绪芝。
吴绪芝在天宝年间长期领兵戍守沙州,精忠报国,战功显赫。
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爆发,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奉命率大军勤王,致使河西势力空虚。
吐蕃趁机剑指河西,一路势如破竹,而吴绪芝率军殊死抵抗十余年,直到建中二年弹尽粮绝,这才选择了投降吐蕃。
投降之后,吴绪芝与吐蕃约法三章,即不迁徙敦煌百姓,不可随意屠戮,不可苛捐杂税等等。
对于啃了十余年都没啃下来的沙州选择投降,吐蕃自然十分高兴,而吴绪芝的条件也被其答应。
也正是因为吴绪芝的条件,这才让沙州的势力没有被吐蕃打乱,给予了张议潮起义的基础。
至于吴绪芝,他虽然投降,但并没有在吐蕃仕宦,而是隐退敦煌乡间。
他的妻子是南阳张氏,与张议潮同宗,因此张议潮在很小的时候就与洪辩结识。
由于洪辩参禅,吐蕃对其也十分尊敬,吐蕃赞普更是下令提升他为释门都教授,成为河西僧界的最高领袖。
期间,洪辩散尽家财,招募良工巧匠开凿七佛堂,历时二年而成。
这七佛堂,便是后世的敦煌莫高窟中的第三百六十五窟,而在此期间,洪辩也借口保护洞窟,招募了许多僧兵。
随着吐蕃赞普被刺身亡,河西局势逐渐变乱,张淮深与洪辩也开始谋划起了起义归唐的事宜。
一直到大中二年,二人决定起义,而洪辩以其河西僧团最高领袖的威望与地位振臂一呼,招募瓜沙等地僧兵蜂起,配合张议潮义军讨伐吐蕃。
在张议潮克复沙州后,洪辩即派弟子悟真等随侍左右,为其出谋划策。
在张议潮收复甘州返回沙州后,便派出了悟真前往长安报捷。
如今悟真归来,说明报捷已经落下尾声,就是不知道悟真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消息。
至于刘继隆在听完了吴氏的起落后,也算知道了吴氏为什么没有子弟担任要职。
说白了,吴绪芝本来就是外来户,只是因为他的身份才能让吴氏成为当地豪强。
可再怎么说,吴绪芝也是外来户,所以吴氏的子弟并不算多,而洪辩参禅,自然不可能还俗。
洪辩不还俗,剩余吴氏子弟没了领头羊,自然只能沉没于历史的滚滚洪流中。
这般想着,刘继隆不免唏嘘。
他并不觉得吴绪芝有错,毕竟他坚守河西十余年,早已经用行动表明了他的态度。
如果不是肃宗不听李泌的,安史之乱恐怕早已平定,而吴绪芝也能等到唐军来援。
想起这些,刘继隆不免惋惜起了如李泌、吴绪芝这些人。
他手下文人极少,崔恕算是为数不多能拿得出手的了。
可即便如此,崔恕也没办法帮他分忧太多。
倘若他手下有李泌这种人,他也就不会被许多琐事牵绊了。
唏嘘之余,时间也不免一点点过去。
从龙首山到山丹二十余里,虽然距离很近,但毕竟下了雨,所以悟真他们今晚估计是到不了山丹了。
张淮深与刘继隆寒暄几句,交代了两日后返回张掖后便去休息了。
张淮深一走,索勋自然没有留下的道理。
随着他们都走了,内堂也再度冷清起来。
曹茂收拾着八仙桌上的茶杯,边收拾边说道:“折冲,内堂什么时候才能有女主人啊!”
“嗯?”刘继隆瞥了一眼这小子,啧啧道:“你想女人了?”
“不是,我是觉得折冲您该找夫人了,我爹像您这么大的时候,我都三岁了。”
曹茂一边收拾一边说,熟练地根本不像个十三岁的少年人。
刘继隆闻言无奈:“刚才张刺史和索折冲在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他们也没有娶妻呢。”
“我不敢……”曹茂笑了笑,刘继隆没好气道:“你是见你家折冲我好欺负?”
“当然不是!”曹茂急头白脸的解释道:“折冲您比较亲近人,张刺史他们不行。”
“呵呵……就当你是夸我了。”
刘继隆靠着椅子笑着回应,心里也在想自己是不是该找个女人。
说到底他也是人,而且是两世为人,自然吃过肉味,有时候想找女人也正常。
只是以他的身份,注定不太可能娶个平凡的女子,所以他并没有着急。
“等你成了丁,我给你说门亲。”
他打趣着曹茂,曹茂却无语撇撇嘴,端着茶壶茶杯去刷洗去了。
见他离开,刘继隆便回到书房练了练字。
他的字不算好看,自然要多加勤练。
如此过了两个时辰,随着天色变黑,他也早早休息去了。
细雨在夜间停下,方便了翌日悟真等人的出行。
待到正午他们赶到山丹时,张淮深、刘继隆、索勋等甘州大小官员已经在北门迎接。
“张刺史……”
“大德。”
悟真和张淮深相互认识,因此二人见面后便行礼表示招呼。
起身过后,张淮深主动为悟真介绍起了所有人。
“这是山丹折冲府都尉刘继隆,我军刚刚出征凉州,收复番和归来,刘折冲在此战中立下大功,获甲三千八百余,为我军重创凉州,明年东进创造了机会!”
“获甲三千八百余?!”
悟真不敢置信的看着刘继隆,他是洪辩的弟子不假,可也是能上阵的僧兵,自然知道获甲三千八百余是什么分量。
要知道他离开大唐时,大唐对党项的作战,先后也不过才获甲六七千,而动用的军队却是甘州的十倍还多。
刘继隆的这份战果,就是放到大唐,也是属于璀璨的将星。
“大德……”
刘继隆对悟真作揖,同时也打量起了他。
悟真留着短须,年纪四旬左右,模样清秀却不瘦弱。
如果刘继隆记得不错,悟真将在往后半个世纪里主持着归义军的外交、僧统等事宜。
他这一生经历了吐蕃治下,张议潮、张淮深、张怀鼎、李明振、张承奉等人统治,堪称归义军内部活化石。
当然,刘继隆之所以记得他,主要还是因为他留下的作品较多,博物馆的《敦煌遗书》中也提及过他的生平。
只是他具体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刘继隆却不太记得了,只记得他应该是在白衣天子张承奉时期去世的。
在他回忆的时候,张淮深也为悟真介绍了其余人。
眼看介绍结束,张淮深迎着悟真等人前往了衙门,而衙门内已经摆上了十余桌酒席。
八十余名将领先后入座,而悟真却诧异看着眼前的圆桌:“这些桌椅倒是新奇。”
“呵呵,都是刘折冲弄出来的,还有等会的炒菜也是刘折冲弄出来的,大德可以好好尝尝。”
闻言,悟真也不免期待起了能让张淮深赞誉的炒菜到底是个什么味道。
不多时,一道道菜肴上桌,有肉有菜。
虽说自梁武帝开始,许多僧人连三净肉都不能吃了,但吐蕃治下的僧人却还是能吃肉的。
悟真没有忌讳,而是动筷吃了几块炒肉,脸上不免浮现笑意:“确实要比一般的菜肴好吃。”
“那您多吃些。”张淮深笑着示意,随后与悟真一边吃一边聊。
二人的话题主要是大唐的情况,其余人也纷纷侧耳聆听,期望听到关于繁华长安,盛世大唐的景象。
“大德,长安是不是繁华无比?”
“圣人长什么样啊?”
“对了大德,关中的百姓和我们这里有什么区别吗?”
“废话!肯定有区别啊!”
“对!圣人脚下的百姓肯定过得比我们滋润多了。”
“大德您快说您快说……”
张昶、马成、李骥等人七嘴八舌的追问着,张淮深与李仪中、索勋也侧目期待。
在场众人,除了悟真和他麾下那十余人,便只有刘继隆沉默着喝酒,其余人目光中流露着好奇与激动。
他们渴望从悟真口中听到当初高进达所介绍的关中与长安,渴望圣明的君王等待他们回去报效。
面对他们的渴望,悟真缓缓将手中茶水放在桌上,抬头与众人对视,眼神淡漠。
“我此行所见的,是跋扈的武人,欺压百姓的兵卒,盘剥百姓的贪官污吏,卖妻儿子女的穷苦百姓,淡漠无闻的上位至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