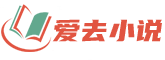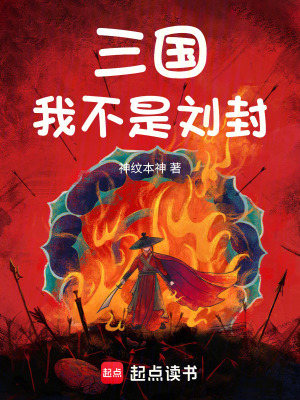第82章 分兵计成,刘封谈笑败三将
即便猜到刘封在营寨中只有四五千人,全琮也不敢再跟刘封在这干耗了。
江津口是必须要救的。
虽说偷袭江津口的汉兵大概率只能袭扰驴车和小船且对江面的大船构不成威胁,但对全琮而言:
丢粮事小,面子事大。
信誓旦旦要生擒刘封,结果一番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0-5,两万大军被刘封遛狗一样遛着玩儿。
全琮还如何服众?
今后一有人提到全琮,就会想到全琮被刘封遛,全琮还要不要面子的?
众小校见全琮发怒,纷纷不敢再言。
在引兵前往江津口的同时,全琮又派人通知丁奉、徐盛和马忠。
并非让三人撤兵,而是将营寨中的虚实告知三人,令三人不可再懈怠。
全琮已经不奢望刘封会弃寨而逃了。
全琮现在只希望丁奉、徐盛和马忠能更悍勇一些,别让战绩太难看。
收到军令的丁奉三人,是震惊的。
打了几个时辰,打的竟然只是个兵力不全的刘封?
尤其是丁奉。
身先士卒的冲了好几轮,本以为对面的俞射只是仗着营寨地利在苦苦支撑,只要再坚持坚持就能攻破寨门。
结果变成了俞射拿着少量的兵力守住了三千人的强攻?
刘封都没用全力?
“这是耻辱!”
丁奉咬牙切齿。
素以勇武扬名的丁奉,自恃勇武不弱于人,结果被一个小小的军侯给拦住了。
不甘受辱的丁奉,不顾军士疲惫,再次喝令强攻。
这不仅仅是全琮的军令,更是丁奉的不甘。
不破寨门,不杀俞射,何以解恨?
东西两门的战事也变得更激烈了,即便是想偷奸耍滑保存实力的马忠也加紧了攻势。
然而。
当吴兵忽然变得凶猛的战况传入帅帐时,刘封的脸上依旧没有任何的慌乱和失措,甚至连一点惊讶和急躁的气息都见不到。
显然。
当前的战况,都在刘封的预料之内,还不足以令刘封意外。
不多时。
北门外的斥候返回:“禀将军,北门外的贼兵正往东南方向而走。”
听到这个情报,一旁的董恢瞬间想到了江津口:“定是江津口遇袭的消息传到了全琮耳中,这支兵马是去救江津口的。将军是否要分兵拦截?”
若是全琮听到董恢的询问,估计人都要气得跳起来,然后揪着董恢的衣襟喝问: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胡话吗?刘封怎么可能还有余力分兵拦截我?
而事实上。
刘封的确还有余力分兵拦截,帐外也还有个校尉邓贤在候命。
在对兵力的调遣上,全琮压根看不到刘封的高度。
兵不在多,在于调遣。
善调遣的,即便手中只有一千兵,也能发挥出两千兵的效果。
不善调遣的,即便手中有两万兵,也未必能发挥出一万兵的效果。
斗将依赖的是个人武勇。
大将依赖的是兵力调遣。
刘封低头沉吟。
刘封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击败全琮,而是夺江陵城,要败全琮容易,夺江陵城却是极难。
需得天时地利人和都恰巧撞在了一起还能被刘封抓住,才能有那么一丝的机会。
就如官渡之战曹操败袁绍时,恰好遇到许攸来投,恰好那段时间没下雨,恰好淳于琼疏忽大意,恰好袁绍军中粮草不足三日,恰好袁绍救援不及时,恰好曹操军粮枯竭不得不殊死一搏,恰好乌巢的距离又足够近,等等各种天时地利人和都恰好聚在了一起。
这其中绝大部分的因素都是无法用人的智力来预料的,机会往往就存在那么一瞬间,抓住了就是万古奇功,没抓住就是兵败自刎。
夺江陵城亦是如此。
刘封不能太急。
若是太急了,时机还未到就会提前将全琮吓回江陵城。
刘封本就是以示弱计才骗全琮生出“我能赢”的念头,才让全琮有勇气留在城外,若一战就将全琮给吓回江陵城了,刘封就难以再有夺城的机会了。
想到这里。
刘封轻轻摇头:“不急。夺江陵城的时机未至,全琮还不能败回城中。”
“传我军令,让寇安国和邓贤引兵反攻东门,破了东门外的吴兵后,立即迂回南门助俞射反攻。”
选择在北门外的伏兵离开后再反攻,刘封也是有考虑的。
北门外的伏兵不离开,反攻的时候就会额外再承受五千吴兵的压力且徐盛等吴兵的士气也不容易溃散,这会增加反攻的汉兵伤亡。
刘封只是不想让全琮被吓回城中,不意味着刘封就得拿汉兵儿郎的性命开玩笑。
寇安国和邓贤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尤其是邓贤。
寇安国还有个巡视四门的军务,多多少少能分到军功,邓贤就纯粹是在“候命”。
这意味着,战事结束后,“候命”的邓贤是分不到任何军功的。
刘备跟孙权在军制和奖惩上有很大的不同。
孙权会根据亲疏来决定奖惩,就如同孙权会将都亭侯给一个身边的马仔谷利却不会将都亭侯给一个打光了部曲的凌统。
刘备则不同。
自底层靠悍不畏死杀出来的魏延当了汉中太守。
每战必先又斩了夏侯渊的黄忠直接加封后将军,且赐关内侯。
常有人诟病刘备苛刻赵云,实则是赵云在入川之战和汉中之战中,立的功劳没有黄忠大。
若刘备因为赵云跟随时间久就加封赵云而以黄忠老迈要死了就无视黄忠的功劳,那刘备就跟孙权封谷利为都亭侯没什么区别了。
这也是为何刘备身边总是能聚集大量肯奋勇杀敌的将士。
哪怕是刘备兵败猇亭后,都还能遇到才能堪比黄权的狐笃投效。
正所谓:上行下效。刘备能严明赏罚,将士自然奋勇争先。
这样的风气,是吴兵不能比的。
故而。
当刘封的军令下达后。
寇安国和邓贤就迫不及待的带兵冲向了东门。
东门的军侯方月得到反击的军令,亦是大喜。
借助营寨的地势跟徐盛斗了这么久,方月的火气也不小。
虽然挡住了徐盛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但没有谁喜欢一直被动防守。
“吴狗虽然人多势众,但军心不齐,只要逮住冲得最狠的打,其余的吴狗就会丧胆!”
方月简明扼要的向寇安国和邓贤归纳了东门吴兵的优劣。
寇安国脱口而出:“这不就是一群流氓混混吗?”
邓贤愣了愣,也反应过来。
流氓混混虽然时常成群结队的看起来凶狠难挡,实际上流氓混混人心不齐,只要将最狠的几个揍了,其余的流氓混混都会作鸟兽散。
“难怪有传闻称张辽八百人就让孙权十万人丧胆还,我本以为这是夸大之词,寇校尉这么一讲,我也就明白了。”
“方才我还奇怪为什么将军一直不肯让我和寇校尉出战,原来是怕出战太早,吴狗败得太快了。”
邓贤舔了舔嘴唇,看向前方的吴兵仿佛在看一个个唾手可得的军功。
寇安国则是用白布将环首刀和右手缠上,盯着徐盛的将旗:“将军的军令是先破东门外的吴狗,再去南门助俞射。”
“速战速决!”
急促的鼓声响起。
得了反攻的军令,不仅方月兴奋,跟着方月一起守东门的军士也是兴奋。
风水轮流转,被动防守了这么久,也是该主动出击的时候了。
此时的吴兵还不知道攻守之势发生了改变。
最前面的徐盛亲兵首当其冲,遇到了刚加入战场的寇安国和邓贤带来的生力军。
忽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徐盛的亲兵也惊呆了徐盛。
徐盛的亲兵之所以看起来最猛,是因为徐盛的亲兵是全琮离开后才加入战场的。
在这之前,徐盛的亲兵一直都是当的督战队。
徐盛这心眼儿也不少。
先让不亲近的军士去前面消耗,等双方都疲倦了再派亲兵上去捞战功。
不曾想这次直接踢到了铁板。
看着一个个亲兵在寇安国和邓贤带的生力军厮杀下负伤倒地,徐盛只感觉心在滴血。
这些亲兵可都是徐盛钱粮厚养出来的,别说死了,哪怕是伤了一个徐盛都心疼不已。
“速速上前支援!”
徐盛赤红着眼睛指挥周围军士,然而周围军士虽然听命上前但一个个又畏手畏脚。
平日里不修恩惠,战场上还被拿刀督战,现在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群甲胄武器更好的,这些军士不是没有情绪波动的机器,自然不可能真的舍己为人。
看着周围畏手畏脚的军士,徐盛又哪里猜不到这些军士的想法。
眼看亲兵死伤越来越多,徐盛一边喝问鼓吹督促周围军士上前,一边让亲卫摇旗语令亲兵撤回。
徐盛想让亲兵退,寇安国和邓贤却不想让徐盛的亲兵退,死死咬住徐盛的亲兵一路追到了徐盛的将旗外围。
徐盛又惊又怒。
倘若徐盛没有受箭伤,必然会亲自提刀壮威,就如昔日在濡须口砍杀魏兵时一般。
奈何如今有箭伤在身,徐盛不敢轻易上阵厮杀。
这也是刘封让寇安国和邓贤先破东门的原因之一,谁弱就先打谁。
见寇安国等汉兵凶狠难挡,徐盛咬了咬牙,转身就走。
好汉不吃眼前亏,徐盛可不想效仿陈武和凌统,在孙权麾下,打光了部曲的将校一文不值。
“吴狗鼠辈,果然不堪一击!”
“众将士,杀吴狗!”
“杀啊!”
徐盛一退,周围本就疲惫的吴兵更不敢阻拦汉兵,纷纷掉头就跑。
寇安国和邓贤没有忘记军务,在破了徐盛后,立即又驱兵入南门助俞射。
比起东门负伤心惧的徐盛,南门的丁奉是块不折不扣的硬骨头。
见寇安国和邓贤驱兵到来,丁奉不仅没有惊惧反而更加悍勇了。
然而。
丁奉再悍勇,也难敌众手。
当寇安国和邓贤加入战场,以及随后东门的方月也引兵来到南门后,双方的兵力差距就不大了。
方月、俞射、寇安国和邓贤四将齐上,也不是丁奉一人的悍勇等抵挡的。
不到半个时辰。
东门的徐盛和南门的丁奉相继被击退,西门的马忠见势不妙,未等汉兵的反攻开始直接就鸣金跑路了。
全琮怎么也没想到。
前脚带兵去救江津口,后脚丁奉、徐盛和马忠三人就被击退。
全琮更没想到的是。
偷袭江津口的李平,不仅没有跑路,反而还在大道设了埋伏,就等着全琮到来。
探得全琮的大旗,李平的眼神瞬间变得兴奋:“本以为只是条小鱼,没想到竟然来了条大鱼,倘若我生擒了全琮,定可助将军定计夺城!”
(本章完)